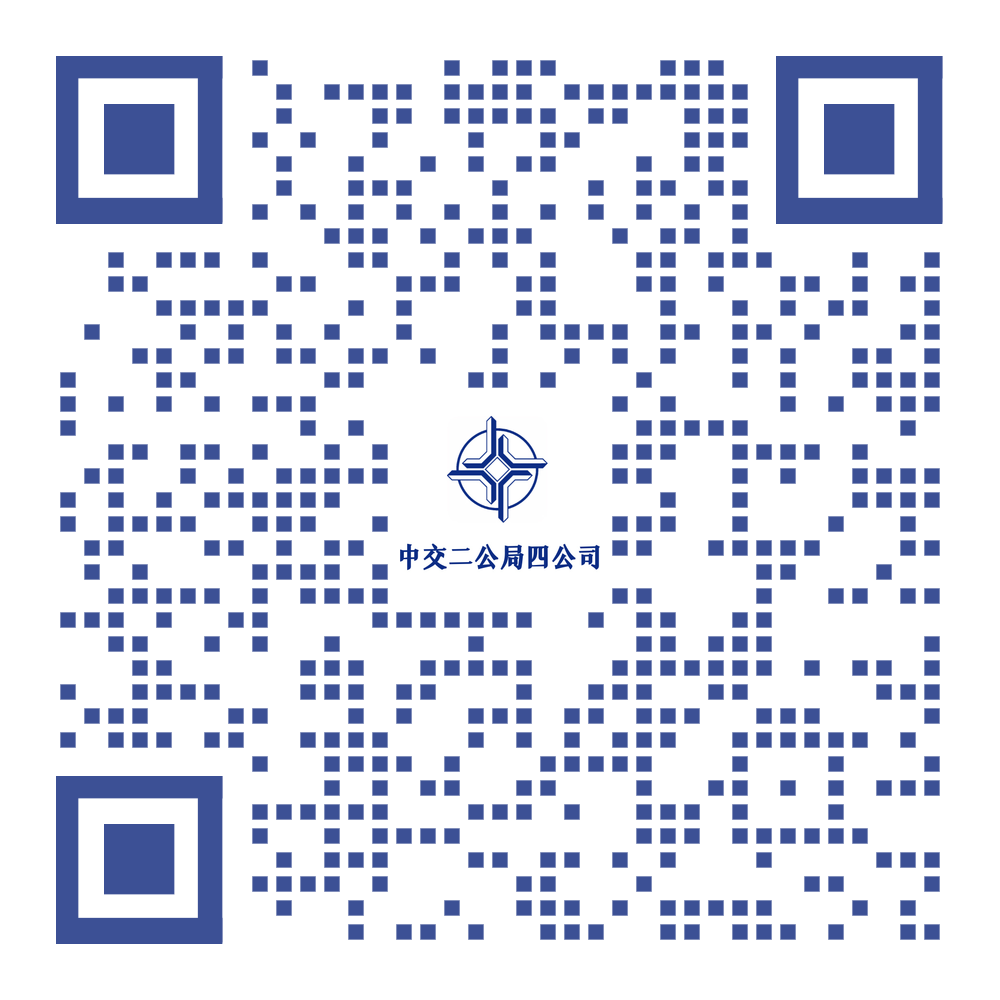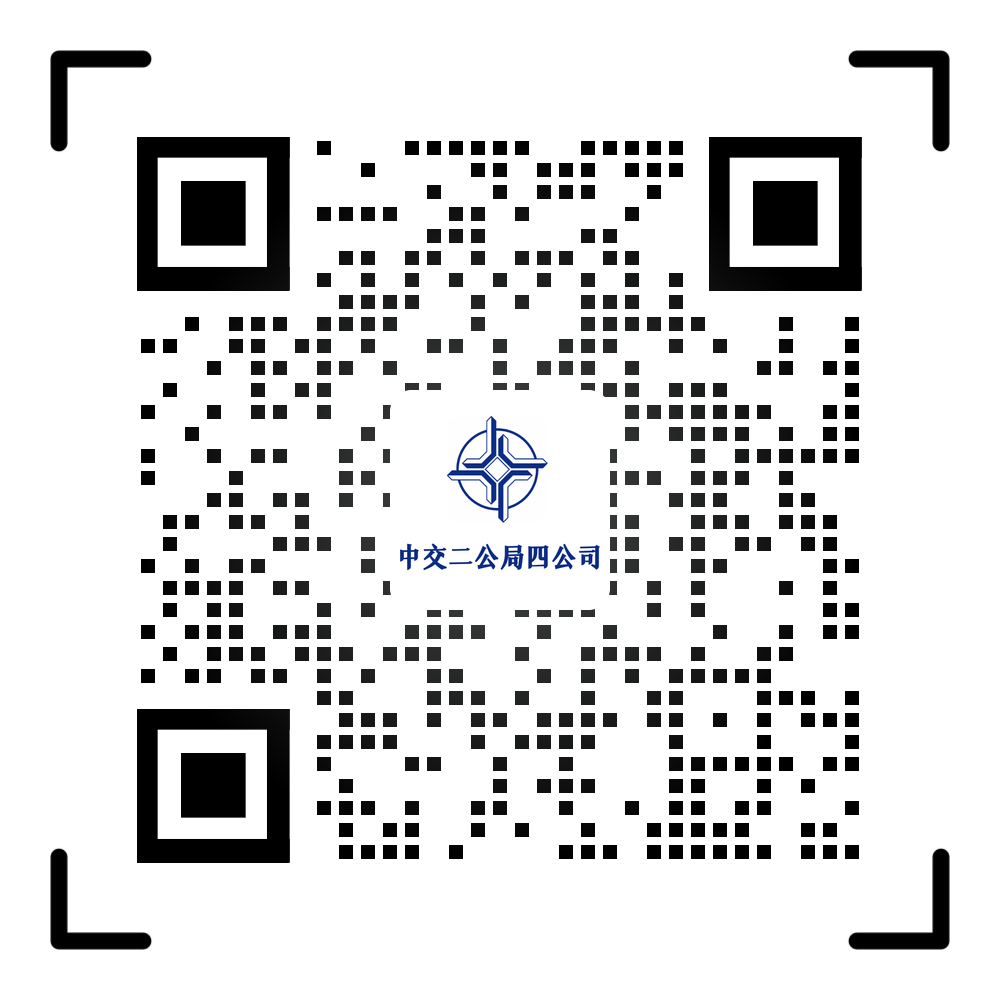综合通讯
一如满月大的婴孩
 2011.10.09
2011.10.09  来源:
来源:  作者:
作者:
来工地整整三十天了,按理说我该写本儿《月子》。
工作之余,我最喜爱的娱乐活动就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大雨天趟着满地泥水piapia的走,或者在萧瑟的冷风中两眼悲伤的看着远处的地平线想,今儿中午食堂做啥。
这大概就是我对悠闲的想象,可悲催的是这世界并不只有吃饭这一件事,而且你越是表现出懒得去想,他们就越凑过来惹你。
想当初,我还是个元气淋漓的小孩儿,脑子里没有所谓成人世界的残缺,唯一能够让我两眼放光的就是油汪汪的红烧肉。那个时候我站在学步车里,顶天立地,只觉得偌大个世界任我行,而最粗狂的梦想就是第一时间花掉手里的每一枚硬币。因此当妈妈把一个重重的陶瓷猪头递给我,一字一顿的教我说“存,钱,罐”,并给我讲解了它的功用之后,我小小的额头上立即渗出了一层汗:这是什么混账玩意,这么反动。当然在这个世界上,幸福的决定权是属于家长的,妈妈她大概觉得,每一个幸福的小孩子都应该有个存钱罐,于是我也就有了,之后妈妈又觉得幸福的小孩应该上重点幼儿园重点小学重点初中重点大学,于是我又一路上下来,可倒也没有什么幸福无比的感觉。后来成熟与长大的我慢慢意识到,当一个人的价值观就维系在某个体系之上时,无论这个体系多么谬误也是不容质疑的。所以父母教育我好好学习,国家教育我晚婚优育,一步一步把我推入拥挤不堪、市侩不已的世俗大河的时候,其实是怀着满心幸福的期待的。
早年我观看电影《毕业生》,一度对男主角达斯汀.霍夫曼的姿态十分着迷。他大学毕业后成天游东逛西,不谋实务,父母怨念:“你到底想要什么?”他答曰:“与众不同。”
我敢说“与众不同”是每一个人都曾有过的想法,因为谁都知道做一个普通人是有多么无聊。十来年前还流行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时候,其实多数人对这种想法持双重态度,一方面戏谑调侃,一方面又望尘莫及。我也尝试过实践这句话,可是当我认识到自己既不是神经病又不是尸体的时候,我遗憾的发现想做到任由别人“说去吧”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这时小表妹边嚼一只卤鸡爪边咕哝:“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我高兴。”不屑之表情很有我当年的神韵,我心里想,孩子啊,当你发现你正做着一件大部分人都不认同的事情时,你基本上是很难高兴起来的。
当下,作为一个合格的人类唯一的任务就是变得成功富有,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权责对等,这就很幸福。基本上没有谁认为除此之外还得来点儿灵魂之受洗什么的,如果有,那叫毛病,这毛病早晚会被日子摆平。所以普通人越来越趋于普通,世俗的河越流越宽广,是有前因后果的。
可我是真不想,在人到暮年的时候发觉自己跟伊凡.伊里奇一样度过了富足却“没什么大意思”的一生,或者“也许自己从未能像应该的那样生活过。”托尔斯泰说:“最简单、最平常的生活,其实是最可怕的”,汪峰唱“我要怒放的生命,我要超越这平凡的生活”估计也是一个意思。
小时候我觉得漫天漫地都是自由,长大我发现漫天漫地的是沙尘暴;小时候我身长一尺可以顶天立地,长大发现自己“日复一日,却从来没有真正生活过。”
现在我二十郎当岁,想法却一如满月大的婴孩,只想世上纵有万般饕餮,我只要一盘简单粗暴的红烧肉,吃的自己满嘴流油,然后朝别的方向狂奔去。(刘 璐)




 返回
返回